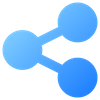圖、文/上報
新自由主義治理之所以強調權力下放,一部分是由於其形式上對中央化國家權力的不滿,一部分則是因為其著重於由利害關係人來解決問題。但被下放的權力與責任不等於全面去中心化或讓地方獲得權力(local empowerment)。權力下放常常代表大規模的問題(如景氣衰退、金融資本危機、失業、環境問題、國家財務危機)被下放至更小且更弱的單位,而無論就技術、政治或財務層面而言,這些單位都無能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國家削減教育或心理健康的資源,並把責任下放至地方,而地方又把責任下放至各別的學校或機構,而其責任又下放至個別部門或系所,而部門或系所裡有一些所謂「決策權威」,但當然,這些權威根本沒有資源行使這種鬼魂般的自主性與主權。
新自由主義治理之所以強調權力下放,一部分是由於其形式上對中央化國家權力的不滿,一部分則是因為其著重於由利害關係人來解決問題。但被下放的權力與責任不等於全面去中心化或讓地方獲得權力(local empowerment)。權力下放常常代表大規模的問題(如景氣衰退、金融資本危機、失業、環境問題、國家財務危機)被下放至更小且更弱的單位,而無論就技術、政治或財務層面而言,這些單位都無能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國家削減教育或心理健康的資源,並把責任下放至地方,而地方又把責任下放至各別的學校或機構,而其責任又下放至個別部門或系所,而部門或系所裡有一些所謂「決策權威」,但當然,這些權威根本沒有資源行使這種鬼魂般的自主性與主權。
「權力下放」就這樣透過增加誘因(而非命令)來讓某些新自由主義改革動起來。舉例來說,我所屬的大學體系在幾年前把給付雇員福利的責任下放給個別的學術單位。這小小的改變開啟了一連串的大學轉型:各個系所開始聘僱更多的兼職學者與行政職員,而如果這些人的工時低於規定時間的一半,就沒資格享有任何一種福利。這種彈性化、不受保障且低薪的勞動力就這樣取代了原先享有基本聘僱保障、健保、失能保障與退休保障的工作。而這當然不是由中央指派或命令的「意圖」。當權力下放至更小、更弱的單位,而這些單位之間又得互相競爭並將自身「企業化」時,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政治學家梭斯(Joe Soss)所描述的治理:「其規範執行力十分強大,但散落在組織各處。」

本書作者布朗以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作為思考起點,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種不斷發展的理性秩序,(春山出版提供)
新自由主義的權力下放與責任化相關,但有所不同。社會學家夏米(Ronen Shamir)將權力下放描述為一種「伴隨政治領域的經濟化而來的、經濟行為的道德化」。所謂「權力下放」即是透過權力與權威的管道下放決策制定與資源管理。另一方面,責任化——尤其是作為社會政策一環的責任化——是這管道末端的實體所背負的道德重擔。責任化要求勞工、學生、消費者或窮人自行辨別正確的自我投資策略,並採行讓自身茁壯與存續的企業形式。人力資本化的過程就在此顯現出來。責任化論述貶低「依存」(dependency),而責任化實踐則否定集體對存在的供給與照應。個體被視為唯一重要且需完全承擔起責任的行動者。治理透過強調共識、反政治、將個體化努力整合進和諧化的目的,來推動責任化的實踐與合法性。如夏米所言:「服從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的萬靈丹,責任化則是治理的萬靈丹。」
這種組織主體行為模式的新權力形態——而治理的重要性就在於激發這類權力——也存在於描述並實行此權力的文法之中。「彈性化」與「責任化」這些髒詞源自某些與最基本的自主性息息相關的人類能力(human capacities)。有彈性或負責任等同於有能力調適或接受問責,而這就如同康德、尼采等人所提醒我們的,皆是主權的標誌:只有出於意願發起行動的道德行動者才能替自身承擔起責任。但當負責任這行為在語言上被轉變為「被責任化」這類被管理的處境時,其便與能動性分離開來,反倒透過外部道德禁令來治理主體—而這種種要求皆源自某個不可見的他方。「責任化」一詞更進一步把有實質基礎的形容詞(負責任的)轉變為奠基於過程的動詞(責任化),亦即把個體能力轉變為治理計畫。在責任化一詞所指涉的體制中,人類獨一無二的負責能力被部署來構築並治理主體,而這能力也被用來組織、衡量、重塑行為模式,使其朝往新自由主義秩序邁進。我們再一次看到,雖然治理助長並強加「責任化」的過程,但我們在論述中卻找不到組織此過程的權力,而權力的消失是新自由主義的常態,也是責任化本身特有的形態。
權力下放不必然等於責任化。我們有別種更能賦權、更具民主潛力的方式來下放決策制定權力。我們要記得,對地方權威與決策制定權威的要求,能同時來自右派與左派、安那其主義者或宗教基本教義派。然而,權力下放與責任化結合在一起後便生產出一種秩序,而權力的社會效應—建構並治理主體—便顯現為背負道德重擔的行動者。能動性與責難被綁在一起後,個體就被雙重責任化:大家期望個體要能照料自己(如果沒辦法茁壯發展就會受到責難),又期望個體要為整體經濟的茁壯而行動(如果沒辦法茁壯發展也會受到責難)。因此,希臘勞工、法國領退休金的人、加州與密西根的公務員、美國社會保險的收受者、英國大學生、歐洲新移民與公共財都被視為小偷般的依附者,不斷享受舊世界的權利而不願照護自己。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斷遭受責難:就是這些人讓國家陷入債務危機、阻礙經濟成長,並把全球經濟帶往毀壞邊緣。最重要的也許是,即便這些人沒有受到責難、即便他們乖乖依照責任化規範而行動,種種以總體經濟健康為名的緊縮措施仍可能正當地摧毀其生計或生命。
因此,責任化的個體因為處在權力與偶然的處境中而無法行使其能力,但他們同時又不斷被要求要照料自己與總體經濟。權力下放與責任化還讓個體變得不受保護且可隨時被犧牲。新自由主義政治合理性的轉向指涉的不僅是鬆動福利國家的邏輯或自由主義社會契約,還是其對立面。
※本文摘自《消解人民:新自由主義的寧靜革命》/春山出版/作者為美國政治理論家,現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UPS基金會社會科學講座教授、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榮譽教授。